|
在被一个疯狂的球迷从背后刺伤之后,年轻的网球明星莫尼卡·塞莱斯遇到了她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对手——恐惧。 飞来横祸 1993年4月30日,在德国汉堡晚春的晚上,天气还有些许凉意。我那时正在参加“城市杯”网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局的比赛。 经过一场苦战,我以6:4的比分战胜了玛格达列娜·马利娃,拿下了第一局,在第二局中以4:3领先,此时比赛暂停1分钟,我正坐在椅子上休息。我用手巾擦去脖子上的汗水,然后将毛巾盖在脸上,俯下身子,将头埋在双膝上,以免分散精力。 突然我感到左背部有一种强烈的难以名状的疼痛——像是灼人的钢针插在背上,我听到自己撕心裂肺的尖叫声。我用手朝背部摸去,竟摸了一手粘糊糊的鲜血!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,朦胧中我看见我的哥哥佐尔坦奔上网球场。“他终于来了。”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,“他会照顾我的。” “一会儿就会好的,莫尼卡!”他说,他按摩着我的双腿,并大叫,“快来人帮忙!” 我喘得厉害,护理人员把我放在担架上,火速送往医院。当我坐在轮椅上被人推进急救室时,我父母都在那儿,他们都在哭,谁也装不出坚强的样子。医生用仪器对我的伤势进行了仔细的检查,攻击者的刀子插入的位置距离我的脊柱仅有几毫米。 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谁,他为什么要刺我?我想:“假如他再来结果会是怎样?”佐尔坦在与一名警官交谈后回到病房,他说:“那个刺伤你的人已被拘留,你现在很安全,可以安心休息了。”我开始发抖,妈妈上床来抱住我。护士拿来两张帆布床给哥哥和爸爸,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在我的病房,像以往一样,我们一起对付所面临的困难。 两天后,史蒂菲·格拉芙来看我,她是我的劲敌,我曾抢了她的世界头号种子选手的位置。她走进病房后,我们俩都哭了。她说:“这种事出在我们国家我感到很难过。”我们交谈后,她还得去打比赛,我表情木然地祝她好运。她一走,我的泪水便像断了线的珠子不住地往下淌。 后来我得知我的攻击者冈特·帕克是格拉芙的球迷。他之所以要刺我是因为我站在格拉芙与世界一号种子选手地位之间。“他的目的达到了,”我心想,“我不能再比赛了,格拉芙将得到第一。” 我被医用飞机送返美国——我和全家自离开南斯拉夫后居住了六年的国家。我们没有回到佛罗里达的家,而是去了科罗拉多的运动医疗康复中心,在那里接受治疗。在乘救护车去医院的路上,我试图让自己不去想冈特·帕克——试图不去回忆他的脸,那沾满鲜血的刀子以及自己的惨叫声。“他们将把他投进监狱。”我对自己说,“我要一心一意地养伤。” 停车场的冠军路 我的网球生涯是在我6岁时开始的,那时看到爸爸教哥哥打网球,也闹着要玩,父亲便开车去意大利为我买回一只小网球拍。在南斯拉夫的家乡,几乎见不到网球场,于是父亲、哥哥和我就在我们公寓大楼前的停车场打网球,在一排排汽车间挂起一张网,我们就在那狭窄的场地上来回奔跑着。今天,每当我听到有人说没有很多的钱就打不出网球来这类话时,我都很不以为然。我生长在前南斯拉夫,那时我们根本谈不上富裕,但我热爱这项运动,而我爸爸则富于创造性和当教练的天赋,这就足够了。 到我8岁时,我已成了前南斯拉夫的少年种子选手;14岁时,我获得了美国佛罗里达州尼克·伯莱特里网球中等专科学校的奖学金。置身于一个陌生语言的国家,我十分思念我的父母。最终我在给父母的电话中泣不成声地说:“要么你们来这里,要么我这就回国去。”我只知道自己当时是一个很不幸福的孩子,我甚至不明白我这是在要求他们辞去自己的工作,告别自己的祖国和朋友。经过反复的考虑,他们决定来美国,这完全是为了我的网球前程,但他们从不对我施加任何影响,无论是赢还是输,我总是他们的莫尼卡。 可是今天,在这里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继续我的网球生涯。 战胜恐惧 1994年3月,我承认我需要超出我的家人所能给我的更大的帮助,心理压力和恶梦总是挥之不去,我的医生推荐我去见心理专家杰里·梅。我向他讲述我反复做的一个梦,在梦中我回到了汉堡的网球场,我出场进行比赛,每当我朝看台望去时,帕克的脸总在那里出现。我要求裁判把那个人弄走,裁判的脸却变成了帕克的脸——脸上浮现着邪恶的微笑。每天夜里我都会被这种梦惊醒,吓出一身冷汗,母亲被我的叫声惊醒,惶恐地站在我身旁。 为了帮我战胜恐惧,杰里·梅教授教我控制意念的技巧。经过几次课后,我意识到正是从网球运动中,我才获得了此生最大的快乐。无论我今后是否还会再度参加网球比赛,我都会热爱这项运动,我需要打网球。 我和哥哥佐尔坦在我家后院网球场开始了训练。 1995年2月,玛尔蒂娜·娜夫拉蒂诺娃打来电话。“我来看你好吗?”她问,“或许我们还可以一起打几个球。”玛尔蒂娜和我度过了非常愉快的短暂时光,午饭时她说:“莫尼卡,你知道,我们大家都想让你重返网坛,我想让你知道,我们每个人都会热烈欢迎你的。”她临走时从腕上取下一只金手镯,“我要你留下这个,它曾给我带来了很多好运气。”她将手镯戴在我的手腕上。 “玛尔蒂娜,我不能接受。”我说。 “当你重返网坛时,你可以再把它还给我。”她笑道。一股暖流涌上我心头,我开始认真考虑复出的事。 1995年4月,德国受理上诉的法官确认了对帕克悬而未决的判决:他因严重伤害我的身体被判有罪,却因精神不正常的理由获缓刑两年。我对自己说:“莫尼卡,你将得不到公正,但无论如何,你得继续前行。” 我安排了7月在大西洋城的一次表演赛,玛尔蒂娜尽管已正式宣布退出个人单打比赛,还是同意了与我对打。比赛的当天我十分紧张,父亲给了我最后的忠告——是一位父亲而不是教练的忠告——“去玩个尽兴吧,是时候了。” 观众席对我和玛尔蒂娜报以雷鸣般的热烈掌声,我打出了几个漂亮的击球,也有几个很欠水准,但最终,经过艰苦的拼搏,我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望一眼眉飞色舞的父母,我跑向球网,拥抱玛尔蒂娜。“你又回来了,姑娘!”她微笑着说。后来我将手镯奉还给她,她是对的——这只手镯的确也给我带来了运气。 大西洋城那场球后,再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去继续我的网球生涯,我参加了8月中旬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国际网球公开赛,打入了四分之一决赛,继而打入了半决赛,最后在决赛中与南非的阿曼达·科泽尔对阵。比赛结束了,我取得了胜利。在看台上的父亲哭了。 当观众的欢呼声如浪潮般涌来时,我的心情十分复杂,我们不再是28个月前的我们,我真正体会到了亲情与友谊的价值。 无论未来比赛再发生什么事情,我都会知道我已经是胜者。 希望还能在赛场上看到你的身影!!!!!!!!
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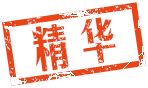
 |手机版|小黑屋|VBOL.cn
( 浙公网安备 33021202000496号 )
|手机版|小黑屋|VBOL.cn
( 浙公网安备 33021202000496号 )